批評的境遇:藝術評論的過去與現在
來源:中國書畫網 作者:編輯-ja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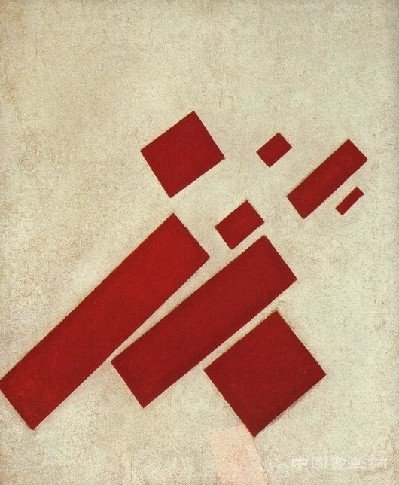
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Artforum》處于第一個全盛時期,為什么這樣說呢?當時的雜志目睹了這些文章的誕生:麥克·弗萊德(Michael Fried)在他的短文中用極簡主義來抗議“物性”(1967年夏季刊),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在他關于主體的筆記中對雕塑進行解構(1966-69各期),洛薩琳德E.克勞斯(Rosalind E. Krauss)對后極簡主義創作的理智與情感從語法上進行分析,當然,這只是其中一些比較突出的例子。刊登的文章對當時的藝術有著犀利的分析,有時可以說甚至超過了它的訴求。在雜志的菲利普·雷德(Philip Leider)的編輯領導下,克勞斯將夸張定為“言論的極致形式”;弗萊德承認同時期的“寫作所承受的巨大壓力”。1 對弗萊德而言,這種壓力產生于“令回應的強度得以恰當表達”的掙扎,從而與相關的藝術力量在修辭上進行匹配。2 但是,懷疑論者卻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例如,湯姆·沃爾夫(Tom Wolfe)宣稱所有的晚期現代主義藝術都是一個批評的騙局,一個“被刻畫過的詞”。3 弗萊德認為這種寫作不僅僅是對藝術的回應,而沃爾夫表示,它還稱不上是批評家的陰謀。而是一個半自動的支持體系,被欲望和野心所支配。“口頭部分,理論部分,懷疑伴隨我左右,”雷德(Leider)曾這樣說過.“每次我對事物看起來的方式,價值,品質,作品的普通特征產生懷疑就如它看我一樣,我就回到思想結構上來。”
通常情況下,晚期現代主義批評與人們所認為的決定藝術命運的批評是不同的(這種差異就如弗蘭克·斯黛拉的可推斷的結構和多納德·賈德的具體物體之間的不同),這些差異常以絕對的方式呈現。毫無疑問,夸張在此是有效的,具體化(hypostatization)也是如此,這是用于批評中的普通變動的尷尬術語,于是,個性化擴大,變成了評判標準。克萊蒙·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最初寫到了晚期現代主義繪畫和它在‘視覺上’的平淡無奇,可以看出,在此,形容詞變成了名詞,特征變成了價值。但是,具體化又是如何產生的呢?這些術語表現了對時代的看法,當然,它們也是處于巨大壓力下對審美領域的維護;其實,它的外部已經受到沖擊,內部已被銷蝕。如我們所知,外在的與之相對的是所說的庸俗(kitsch),戲劇化,或簡言之,大眾化,(波普在這里成為公開的背叛者),而內在的敵人則是偶發藝術,激浪派,極簡主義所打開的藝術活動的競技場。對于后現代主義批評家而言,這些活動都有問題,不僅是因為它們超越了繪畫和雕塑的常規媒介,而且還因為它們在將藝術推入一個超越審美判斷的任意范疇里。
這種任意性對藝術家而言也很刺目。如果一些人通過改良晚期現代主義繪畫,從而抵抗這種任意性,那么,另外一些人則在新材料和過程的絕對真實性或藝術家和作品場所的絕對真實性中尋求積極的動機。5 諷刺的是,即使這一后來的創作項目想去重新激活藝術,重新給藝術尋求根本,努力將自身的創作和意義以更顯著的方式表現給觀眾,但產生的效果卻往往是相反的:藝術看起來更加隨意了,藝術的特性變得稀薄而難以辨認。諷刺的是,在所蘊含的意義上,之前的創作并沒什么不同,因為對晚期現代主義繪畫的改良無法對這種藝術的決定性本質(如格林伯格所想)、它必要的常規性(弗萊德對此的糾正)、以及它能夠被共同分享的意義做出解釋,這里的分享受眾指的是比《Artforum》忠實的讀者群范圍要更廣的大眾們。7所以,藝術的運行變得更具多樣化但又日益難以識別,令人信服的論證變得迫切起來,同時也受到了限制。“這是一個企業,”弗萊德在1971年關于莫里斯·路易斯(Morris Louis)的文章里這樣寫,“如果不受到道德和知識熱情的啟發,注定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沒有受到道德和智力偏見的力量的左右,那么注定是失敗的。”6托馬斯·克勞(Thomas Crow)后來對這一聲明進行了簡短的解釋:“現代主義批評令六十年代承載了過多的道德負擔,它曾經作為理想的公眾領域的重心,是早期藝術夢留下來的殘余物。”7
這里所涉及的不僅是審美特征化身為批評的價值,而是道德,知識和政治任務的替換。弗萊德在他1965年的文章《三個美國畫家:肯尼斯·諾蘭德,朱爾斯·奧列斯基,弗蘭克·斯黛拉》(“Three American Painters: Kenneth Noland, Jules Olitski, Frank Stella,”)中,指出了這一置換,但卻并沒有說太多。他寫到了“現代主義的辯證”是與黑格爾-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觀一致的,鑒于此,通過對每個嶄新的重要歷史關頭的“激烈批評”,就產生了托洛斯基式的“永久性革命”。
弗萊德總結道:“毫無疑問,這一理想并未在公眾領域內實現,但對我而言,過去一個多世紀的現代主義繪畫的發展已經形成了這些術語所描繪的一種情勢。”8 五十年過去了,這一宣言令人發笑,流淚,對其當年的自信滿滿感到訝異,對所蘊含的信念心懷敬仰,或者,僅僅只是憐憫的笑或嘆息。但它在今天,依然對我們具有震撼性,弗萊德將現代主義繪畫理解為其它方式手段的辯證的持續(更確切說,作為它重大損失的部分補償),這一論斷多么積極樂觀,憑借于此,社會生活中的永久革命也許可升華為藝術形式的永久革新。
這種置換作為現代宏大敘事的后現代批評的對象而被質疑。我們將這種置換批評為逃脫甚至是詭計,我們經常忽略了它努力要保留下來的那些,比如藝術家和評論家的基本期待—-去努力解決(從某種意義上講,既是弗洛伊德式也是黑格爾-馬克思主義的)他們胸懷抱負的前輩們所棄掉的那些重要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個說法:藝術和批評也許依然—-如果不是歷史的中介—-至少還是歷史發展變化的索引,因此也是與這種變化的文化重要性有關的批評藝術形式(為什么說任意性對這一觀點產生威脅,這就很清楚了。)作為抓住過去的一種手段的藝術和批評,面向的是現在和未來:如今這種觀念幾乎很奇怪了。我們可以隨意指點它,說它天真,狹隘,空想,我們可以將其貶為某種愿力渺小的表達,藝術史就以這樣的方式被解讀著(只有少數北精挑細算地留下來,其他的每個人都出局),進入到當代創作中來,然而四十年來,我們也應該知道,當這一觀念被丟棄后,究竟失去了什么。
注解:
1.艾米·紐曼,《挑戰藝術: Artforum 1962–1974 (紐約: Soho Press, 2000), 152, 187.
2. Ibid., 187.
3.湯姆·沃爾夫, 《被刻畫的詞》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75).
4. 紐曼, 《挑戰藝術》295 (原版).
5. 見羅伯特·莫里斯,《制作的現象學筆記:尋求積極者》, Artforum 9, no. (April 1970): 62–66.
6. 麥克·弗萊德, 《莫雷斯 路易斯》選自《藝術與實物》 (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98), 101. “令人信服的論證“是弗萊德式說法。根據他與哲學家斯坦利·卡維爾的對話,這一艱難的情況正是現代主義所處的環境,現代主義藝術的一個目的是對它的意義和觀眾的理解力,進行一遍遍的考驗。
7. 托馬斯·克勞,《三個收藏家,他們現在談論Baudrillard》 in Hal Foster, ed., Discussions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Seattle: Bay Press, 1987), 7.
8.弗萊德, 《三個美國畫家:肯尼斯·諾蘭德,朱爾斯·奧列斯基,弗蘭克·斯黛拉》
來源:藝術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