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版畫目前在發展中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缺失:一是評價體系的缺失,即學術建設基礎較弱;二是市場行為的缺失,即版畫的社會影響力較弱。這兩點都會影響中國版畫將來的發展。同時版畫觀念、語言、風格三個方面的問題,也制約著版畫的發展。歷史觀念相對保守,讓畫面缺少時代的關注點;表現語言過于雷同,讓敘述缺少語言個性;風格氣質庸常貧弱,讓精神張力難以舒展,這些問題明眼內行都不難看出,在表象之后,版畫除了因版成畫這個客觀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審美理念的歸向以及在文化意識、思想維度和精神品質上的追求。

最近,我看到一些令人欣喜的版畫作品。比如羅貴榮的套色凸版版畫《時間·時間》 ,以一種新穎的立場、幽默的敘述、飽滿的色彩和獨特的角度,表現了新時代的路橋建設;作品跳出了作者自己熟悉的表現慣性、溫暖的語言巢穴,從意境到情致跟以往的自己都大不一樣,是在新時代現實基礎上的再出發。同曲異工的還有曹丹的凹版版畫《陽光下的大橋澆筑工》 ,畫中工人的形象樸實生動,凹版細膩的語言風格蘊含了時代的寫意精神。
然而,還有相當多的版畫作品還停留在“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的階段。歷史觀的局限導致認識論的滯后,認識論的不足又影響到語言的進步,共性化的語言占比很高,而個性化的語言很少。很多作品就故事講故事,無法從故事的情節性、再現性上浮到意義層面,更談不上從人的行為方式中精粹出時代的人性精神。要知道,故事就像螃蟹,形狀描述和味道品鑒務必要形成從視覺到味覺聯動,才能完成審美的驅動。形態描述得再具體、再細微,最終都要“入嘴為安” 。藝術以審美的名義展示人性的永恒,化解人類行為的迷茫。版畫創作不能總云山霧罩地講故事,要從故事中提煉出人性的品質和操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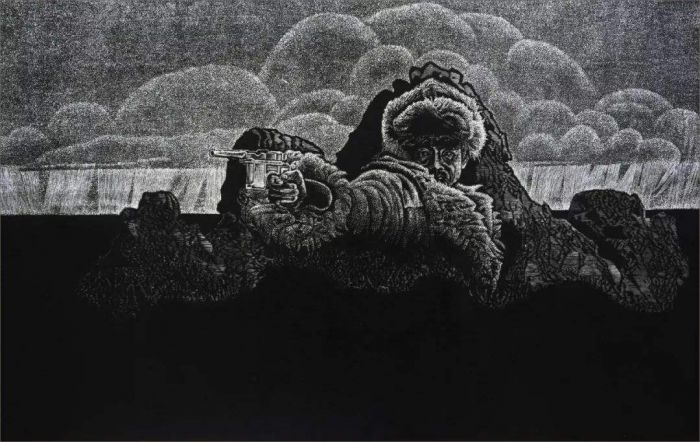
再進一步談談形象的概念化,因為這影響著許多觀者對作品更深入閱讀的審美快感。概念化的物象與人形,注定只是表面化的膚淺表現。共性可以講述故事的一般框架和概念,個性才能體現故事的獨到之處和真實目的。生活給予畫家的啟迪因人而異,一般人很難從豐富的生活中提煉出不一般的所在,這也是藝術的作用和意義。
有一個不好的現象是畫家把自己當成勞動模范,以密集鋪陳替代聚精凝神。畫面的豐富性不能以堆砌為能事,還應該去引申和塑造理念,引導觀者從表象走近實質,否則視覺的豐富就無法構成想象的空間,無法達到意境的詣趣。這幾年,用體力而不用腦力畫畫的人越來越多。以版畫為例,現代科技工藝的進步,使得相機取景、電腦成幅、數碼打印更便捷。相機取景框定了觀察,電腦成幅決定了視像,數碼打印疏離了行為——這是用邏輯程序取代人的思維。邏輯程序不允許意外和偶然,不存在試錯空間,所有意外都在軟件編程過程中被嚴格計算掉了。
中國古人對藝術的最高評價是奇思妙想。眼前的人形物象不過是想象的起點而非終點,莫名其妙和匪夷所思的“妙”和“思”在藝術創作中是最難的。而今,創作中呈現的變化是程序軟件所設計的,實際上是用更豐富的共性再現替代了更獨特的個性表現。版畫是繪畫品類中最早“中毒”的,甚至發展到用數碼打印和激光電刻完成作品。如此看來,用“相機取景+電腦編程+激光合成”這種最現代的技術、最現代的版畫實際三五天便可煥然問世,這是目前存在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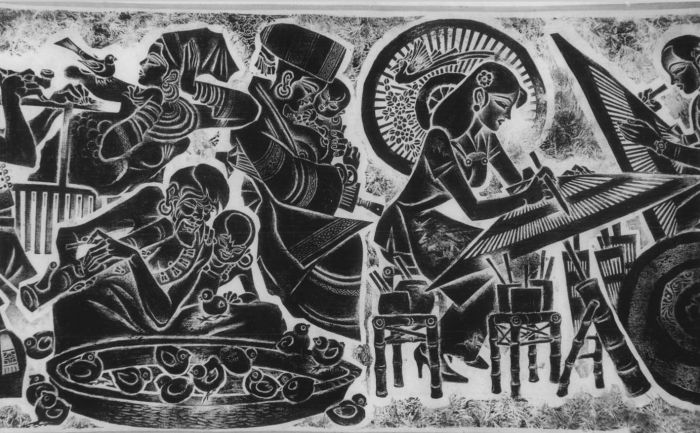
最后講講版畫的邊界。藝術表現本身是不應該人為地設定邊界的,但藝術語言的個性特征又決定著它的審美趨向。個性越多元,共性越豐富;語言越有特點,表述才越生動。創作可以有不著邊際的探索,也應當允許一定之規的執著。歷史與現實要有機融合,創作者應“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 。
(圖片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