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美俊:書畫創作的個體與集體意識
來源:中國書畫網 作者: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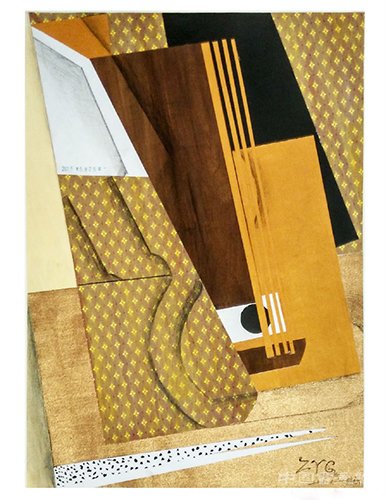
張雨舸無題(紙本拼貼繪制),2015年,四川大學錦城學院
無論是肉身、思想還是藝術風格,書畫家既是個體的,又是集體的。之所以是個體的,書畫家生而自由,創作無需看他人臉色行事,可以隨心所欲;之所以是集體的,書畫家往往有供職單位,有或大或小的專業圈子與人際關系,因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除非書畫僅為自娛也一輩子甘當隱士,否則師承淵源、創作題材與風格什么的都得識相,得合群抱團,得與時俱進,得為悅己者容,得為展覽、市場或是某些指示而妥協。
顯然,美術史上不乏由機構牽頭體現集體意志并組織創作的先例,也不乏優秀作品。比如,北宋徽宗時期的翰林圖畫院施行皇帝審稿制,縱觀其治下的作品,雖不乏《瑞鶴圖》等粉飾之作,整體藝術水平及趣味并不俗。再如,清代乾隆帝曾命金昆等十余位宮廷畫家畫《大閱圖》以弘揚國威。而新中國建立后,由文化機構、協會、畫院等組織的主題創作,以及前些年實施的“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都有群策群力的集體努力的影子。董希文的油畫《開國大典》,楊之光表現老婦拿到選民證欣喜若狂的中國畫《一輩子第一回》,以及宣傳黨的養豬方針的《養豬印譜》,有的雖系個體創作,但都有著集體的合力,而且都符合時勢的要求并有著鮮明的時代記憶。
盡管如此,我認為創作還是要提倡個體意識。藝術工作者,在西方是毫無疑義的自由職業者,自身是自由的個體。能夠在書畫史上留名,在我看來主要取決于兩點:一是自身取得的專業內在邏輯的高度及影響力,再是與時代社會的契合度及被選擇的可能性,時名與史名也未必會一致。前者如清代“四王”及張宗蒼的集成式的也算不俗的山水創作,他們曾深得清廷恩寵,不過以創新、個性等視角觀之,比同時代的“四僧”、“八怪”則略微遜色。后者如被稱“中國最后一位傳統詩人”的陳三立,其詩作水平不輸唐人,卻無法撼動唐詩的經典地位,當時的文學主流已是新詩及新文學,其個人努力與時代選擇錯位了,甚至沒有一首詩被廣為傳頌。
誰都不想被時代拋棄,得契合時代融入某些圈子,享受到所謂的“集體溫暖”。就像民企與國企的某些不對等待遇,目前書畫界生態中的個體藝術家處境尷尬,自是無法與某些“集體”中人相比。長此以往,讓人遺憾的逆淘汰現象也就不可避免。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以私人趣味畫點花花草草,除非特別出色否則很難有推廣價值,這也是解放后潘天壽等花鳥畫家的郁悶之處,不得不蹩腳地隨大流畫點《送公糧》等具有時代性的人物題材。而有的花鳥畫家無人物造型能力,就只得迎合時勢畫些討口彩式的花鳥畫題材了。比如《又紅又專》,往往畫一塊紅磚壓在一竿竹枝上;再如《戰地黃花分外香》,多畫數叢黃花或是掩映在黃花間的槍支彈藥及水壺什么的。這樣簡單明了的隱喻在當時確實能贏得喝彩,而如今看來卻多少有些以圖釋文的機械比附。“專”指的是專業,非磚頭的“磚”。當然,如果以磚代稱那些有“專家”身份卻無專業水準者為“磚家”,倒也是準確的。“戰地黃花分外香”語出毛**《采桑子·重陽》詞,我看過一些資料,并非是指戰地野菊花澆灌了志士仁人鮮血,在烈火硝煙中特別的金黃芬芳,而是指慘烈戰斗后黃銅制造的子彈殼遍布戰場,這在勝利者的目光看來,自然是燦爛如花芳香無比了。
但是,融入時代與集體的創作也并非是機械迎合時勢,如果創作接地氣也算不錯,否則很可能淪為假大空,還自以為是弘揚正能量、批判假丑惡。文革期間盛行“政治掛帥、主題先行”套路,一些極端甚至是偽歷史畫創作的教訓是慘重的,藝術成為某些戰線的“斗爭”工具,還自以為是正確的創作道路。在那個不正常的時代,一些水平一般的作品借助公權力的推廣,頓時變得無比“優秀”甚至神圣起來,藝術家因此一炮而紅。在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下,一些與“優秀”作品風格不符的則被打成毒草,甚至形成今人難以想象的規模化“批黑畫”運動,從而強化了“紅光亮、高大全”的狹窄創作時風。
時下個體書畫家的處境并不樂觀。比如,申報藝術基金或課題,無單位推薦連資格都不具備;想發表論文,如無博士學位或副高職稱,連投稿資格都沒有。青年版畫家葛冰的作品《民族脊梁——陪都國立藝專七任校長》曾獲“第21屆全國版畫展”優秀獎。他的老師、西南大學的戴政生教授對這位才華初露但生活困苦的年輕人推崇有加,但因其無博士學位而無法留校。如果他不能進一步享受到“集體溫暖”,沒有與專業相合的職業及收入,其冷門而且燒錢的版畫創作將無法繼續。盡管,已享受到溫暖但如吳冠中批評的“不下蛋的雞”也并不少。從這個意義上說,集體的影響力會遠遠大于個體努力,也難怪有人會削尖腦袋進入某些體制化的機構及關系圈,也難怪現在到處是“畫派”打造及攀龍附鳳式的“名家班”之類的東西,其根本原因是渴望在集體的內部利益均沾,以尋求更好的發展平臺。畢竟,任何成功書畫家的途徑,不外乎策展、征稿、創作、展出、宣傳、入藏等關節,每一關節既關乎個人努力,更有某些圈子化及集體利益的影子。在發達的商品社會,力量強大的資本含與資本結成的權力關系,其作用往往會大于生產和流通等環節,可以配置資源、組織生產,甚至控制商品的流通與消費。近年來某些機構或傳媒,則扮演著“資本”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主宰和引導著文藝的投資、生產、消費與流通。有人說“能力之外的資本等于零”,此話雖勵志但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恰好相反,而是“資本之外的能力等于零”。個體書畫家如不在某些集體中,含主動進入或被遴選,就自然會被邊緣化。近年來政府繁榮地方美術文化,經濟扶持與贊助政策開始流行,創作、展覽及研究只要符合相關條件并加掛某個由頭就可以申報成課題或項目,獲得從幾千元到數十萬元的資助。這本是好事,但也會有硬幣的另一面,會導致揣摩上意,扼殺藝術個性,甚至催生出一些與藝術毫無關系的利益交換的“生意”,而時代呼喚的力作及研究成果并沒出現。
今之好萊塢電影、娛樂電視節目,各種美展、藝術節等等,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運作模式,自然會或多或少碾壓甚至取代藝術家的個體思考。以書畫展覽為例,前些年黃賓虹熱、流行書風熱,近年來的水墨熱、“二王”熱,創作者不諳時勢還執著于自己的理想藝術天國,往往會發現自己作品的風格與時下展覽體制下的作品格格不入。無須諱言,在商品大潮與便捷資訊的時代條件下,個體的堅守會異常困難,盡管你也如吳冠中那樣非常厭煩展廳中那些“戴著面具跳舞”的作品,但糟糕的是你并不是吳冠中。而古代書畫創作個體命運卻不是這樣,售賣書畫為生的人當然有,不以此為生的人也多,因此書畫的自律發展得到某些保證。即便是出售書畫者,也未必完全按照市場規則辦,比如脾氣頗怪的徐渭,求其書畫者,一定在其缺錢時投以金帛甚至是提供簡單餐飯方可稱意,反之,即便以重金相賄仍不可得。其開創性的狂草書法、大寫意花鳥畫的貢獻,也就因此成為可能。
無疑,藝術的發展既非完全自律,更非完全他律。多元時代的個體藝術家注定是孤獨而困惑的,而又如何平衡創作與各種他律性因素的抵牾并存活下去?我還是認為,關于藝術創作社會還是要更加尊重個體創作者及藝術本身,作品的藝術價值、歷史價值、市場價值什么的,其實與供職單位、職務職稱、社會功名及機構組織等關系真的不大。而創作者呢?也未必老是去察言觀色,想著代國家及時代立言這樣的宏大目標,只需做好分內之事靜待時代的選擇即可。某些美術機構號稱“對內代表國家,對外代表中國”,國家這么大、美術從業人員這么多、風格這么雜,你能完全代表?因此,某些集體性的“代表”,即便獲得時名與時利,也未必能夠青史留名。畫史上的中國歷代皇家畫院,也非任何時代都是當然的正史,如明代中后期的宮廷畫院,其創作水平與地位根本無法抗衡吳門畫家,甚至此前以戴進、吳偉等為代表的院體別派——浙派,其藝術貢獻也不輸當朝畫院。因此,藝術家在創作時,更需強調在自己理解范圍內的個體奉獻。唐人孫過庭在《書譜》就指出了這兩種人的命運:“或藉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無疑,歷史是公正的,重要的還是藝術本身。比如,文革時期的美術時風,并沒有掩蓋住林風眠、陳子莊、黃秋園等人的不為時尚所動的個體艱苦探索。
時下的書畫家似乎可以也考慮長遠一些:不為時風流俗、功名利祿所綁架,以個體的藝術思考去契合時代。似乎,個體的藝術家也可以做到。
作者:范美俊 來源:《北方美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