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畫網(wǎng) > 藝術(shù)資訊 > 收藏 > 老舍在美遺失的英文譯稿被發(fā)現(xiàn) 《四世同堂》齊全
老舍在美遺失的英文譯稿被發(fā)現(xiàn) 《四世同堂》齊全
來源:中國書畫網(wǎng) 作者:網(wǎng)絡(lu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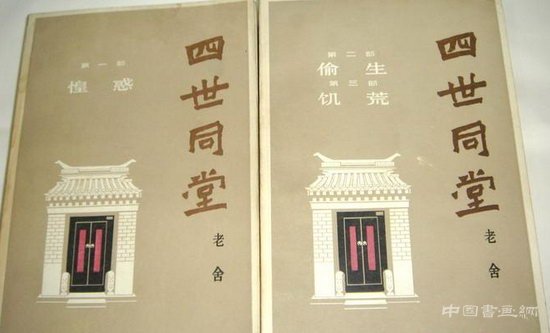
1970年代,百花文藝版《四世同堂》
董子琪
日前,作家老舍在近70年前在美遺失的《四世同堂》原稿,已被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社長趙武平找齊并譯出,未曾出版過的《四世同堂》21-26章、約十萬字將全文刊登在2017年1月的《收獲》雜志上。這將是老舍先生這部巨著第一次以本原面目示人,意義重大。《四世同堂》作為老舍一生最重要的作品,經(jīng)歷了怎樣的出版和譯介歷史?這次又是如何被重新發(fā)現(xiàn)的呢?
《四世同堂》從未完整地出版過
《四世同堂》是老舍一生最高的文學成就,全書分《惶惑》《偷生》《饑荒》三部,遺憾的是,第三部《饑荒》從來沒有完整地出版過。1945年,老舍在《四世同堂》的序言中寫道:依照計劃寫來,第一部為34段,后兩部各為33段,最后合在一起,全書100段。(注:此處的“一段”指一章。)
第一、二部《惶惑》和《偷生》1944-1945年間在重慶《掃蕩報》和《世界日報》副刊連載,1946年得以出版。此后,老舍接受美國國務(wù)院邀請赴美,第三部《饑荒》是老舍在美國期間完成的。《饑荒》的前20章內(nèi)容于1950-1951年間在上海《小說》月刊連載發(fā)表, 但因為各種歷史原因,最后13章并未出中文版,后來文稿于文革中被毀。1951年,《四世同堂》英文版在美國出版,為我們?nèi)缃裱a齊和復原該書留下了一線希望。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孫潔在《有生之年! <四世同堂>!更了!》中說,1981年,人們發(fā)現(xiàn)了經(jīng)過縮略處理的《四世同堂》英譯本的最后13章,由馬小彌轉(zhuǎn)譯為中文后,發(fā)表在了1982年第二期《十月》雜志上。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四世同堂》時,采用的也是這由英文版回譯的13章文字。
就此,《四世同堂》一書貌似已然齊全,但事實并非如此,因為《四世同堂》第三部最后的這13章是根據(jù)英文譯稿回譯而來,而英文版是經(jīng)過了美國出版社與編輯大量刪減后的“閹割版本”,并非老舍原稿。
《四世同堂》的英文全本是如何找到的?
2013年5月,在美國訪學的趙武平通過網(wǎng)絡(luò)檢索發(fā)現(xiàn),哈佛大學施萊辛格圖書館的浦愛德檔案中可能保存著《四世同堂》的美國檔案,包括老舍在美國創(chuàng)作完成《四世同堂》第三部后尚未發(fā)表中英文版之前的全部內(nèi)容和譯者資料。
浦愛德是誰?根據(jù)施萊辛格的檢索檔案,浦愛德是《四世同堂》(1951)的譯者。我們可以從2012年彭秀良的《被塵封的國際友人浦愛德》一文中看到浦愛德與老舍的關(guān)系:
“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九月間,旅居美國的老舍與浦愛德一起翻譯了《四世同堂》,該書于一九五一年以《黃色風暴》為名由美國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翻譯過程是比較獨特的,先是由老舍對小說進行刪節(jié),然后再口授給看不懂中文的浦愛德,由浦愛德錄于紙面。”
這段記錄既說明了浦愛德的身份,又點明了《四世同堂》是由浦愛德和老舍共同合作翻譯的結(jié)果,而且,浦愛德英譯根據(jù)的是老舍未刊登的文章原稿——這是目前世界上最接近老舍原作面目的版本了。
《四世同堂》英文譯者浦愛德
編號為MC465的浦愛德檔案共有11盒,《四世同堂》的數(shù)百頁材料分裝在常規(guī)檔案盒中,內(nèi)容分兩部分:一為全部譯稿,二是同翻譯和出版相關(guān)的通信、筆記、卡片和零稿等雜項。
從趙武平的《 <饑荒 >回譯記》中,我們可以一窺當時《四世同堂》英文譯稿被發(fā)現(xiàn)時的樣子:“(文稿)打印在相當于A4紙張大小的、薄近透明的白紙上;文稿按先后順序,每兩章,或三到五章,整整齊齊分組裝于三十個乳黃色的文件夾內(nèi)。譯稿有三部分,即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初譯稿,以及初譯稿若干零頁,稿面上有繁密的改動筆跡, 字體潦草,難以辨認;第二部另有一份修訂謄清稿,篇幅從三十二章,縮至三十一章;以及第三部,也就是《饑荒》的全譯稿。 ”
第三部《饑荒》英文譯稿共36章,比原先中文版回譯時參考的刪減版本多出9章,比老舍原定的30章還要多出3章,經(jīng)過對比可以發(fā)現(xiàn),之前發(fā)現(xiàn)的“后13章”,就是由這16章壓縮和刪節(jié)而來的,比如第23章“東陽病了”壓縮后同第24章“冰化了” 并為一章,第27章和36章整章刪去,還有部分人名有了改動。如果《饑荒》后半部第21至36章回譯為中文,加上之前已發(fā)表的20章,可知全書大約21萬字。
這雖然已是我們能找到的最接近老舍原稿的版本,但嚴格說來也不是全本,因為它也經(jīng)歷過刪節(jié)。“應(yīng)該所刪只是枝節(jié),或者意義較輕的段落,起碼沒有改變結(jié)構(gòu)。”趙武平推測道,并引用浦愛德晚年的信件說明:
“老舍知道,美國人不喜歡篇幅太大的長篇小說,所以我們一起工作時候,他對原書作了較大的刪節(jié)。不幸,出版社刪得更多,一個完整的人物被刪去——雖非主要人物,卻是我最喜愛的人物之一,就是那個照應(yīng)墳地的種地人。”
除了譯稿部分,《四世同堂》的信件部分還有浦愛德的合同、版稅單以及她與編輯的通信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檔案里還有一份夏志清的致信。
這封“文學求助信”是夏志清1960年8月寫給浦愛德的,當時夏志清還在紐約州立大學英語系執(zhí)教,他的專著《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還未完工。在信中,夏志清提出,希望可以看到《四世同堂》第三部的出版信息,還想從浦愛德那里得到《四世同堂》的英文譯本《黃色風暴》。
根據(jù)趙武平的推測,夏志清很可能沒有收到浦愛德的回信,最終無緣《四世同堂》的第三部全稿,這也影響了他對于老舍文學成就的評價,甚至影響了之后李歐梵等人對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評價。
《四世同堂》如何回譯為中文?
70年過去,打印稿上已有不少字詞褪色、難以辨識,加之拼寫錯誤等因素,要將浦愛德的英文版回譯為中文,趙武平認為這項工作是“曲折、復雜而處處容易陷入誤區(qū)的”。
“首先,要針對英譯原稿,逐篇進行釋讀,錄下所有難以辨識的文句。經(jīng)過近七十年的時光磨蝕,打印稿上不少字詞已經(jīng)變褪色,甚至模糊;另外一些,是打印中的拼寫錯誤,再者就是譯文中所運用的今天已經(jīng)廢棄使用的日語拼寫,這占去了前期翻譯的大部分精力——后來,為了解決其中疑難,去年我重新回到施萊辛格圖書館,再次檢閱了原稿,同時就其中日語詞匯,請教了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日本專家傅高義教授,和負責出版事務(wù)羅伯特·格雷厄姆先生。”
老舍是個語言大師,為了讓用詞和表達方式貼近老舍的語言風格,趙武平整理出了“老舍詞匯表”,比如他更常用“假若” 而很少用“如果”,他會用“助援”而非“援助”、自傲而非“自豪”、“羞惱成怒”不作“惱羞成怒”。老舍似乎不太喜歡運用習見成語:他用“咬著牙說”不用“咬牙切齒”、用“忍受苦痛” 不用“含辛茹苦”,用“設(shè)盡方法”不用“千方百計”。 此外,趙武平還從《駱駝祥子》里借用了個別詞匯,比如譯稿里說白巡長被“撤了差”,就取自《駱駝祥子》開篇部分的一句話:“被撤了差的巡警或校役”。
在上世紀80年代從英文縮略版回譯的版本中,老舍夫人胡絜青曾寫下一段感言:“不久的將來,可能會出現(xiàn)一種新的《四世同堂》版本,它既包括目前出版的最全的中文單行本的全文,即按老舍中文手稿排印的前八十七段,也包括由英文節(jié)譯本轉(zhuǎn)譯回來的后十三段,全書共一百段,正好是老舍原來計劃和實際完成的一百段。” 現(xiàn)在,因為新譯稿的發(fā)現(xiàn),《四世同堂》已經(jīng)有了一百零三段,這雖然不是老舍計劃中的手稿的全部,但也可以讓新一代的讀者更加接近老舍的原作。新版《四世同堂》預計將于明年2月由活字文化出版。
本文部分參考了趙武平《 <饑荒 >回譯記》,由作者本人授權(quá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