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了美術館,會好看起來
來源:藝術中國 作者:admin

人到了美術館會好看起來——有閑階級,閑出視覺上的種種效果;文人雅士,則個個精于打扮,歐洲人氣質尤佳。
——陳丹青
也許每位藝術家的骨子內都是不羈的,但陳丹青的不羈已經分分明明地鐫刻在了他的文字當中,抑揚頓挫的語調仿佛粗糲率性的木炭筆觸,在讀者的心頭勾勒出犀利卻也不乏睿智的批判者形象。短短數段內,陳丹青用語言難以到達的逼真效果回憶起青年時代在美術館度過的美好時光,娓娓道來,引人入勝。
以下內容摘選自陳丹青《紐約瑣記》

大都會博物館 1982年
孩子喜歡打量穿制服的人,我也喜歡。在這兒,警察的黑制服和一身披掛當然最醒目:帽徽、肩章、警銜、槍、子彈帶、手銬、警棍、步話機,外加一本記事皮夾。有一回我在地鐵站點煙,才吸半口,兩位警察笑嘻嘻走攏來,老朋友似的打過招呼,接著飛快填妥罰款單,撕下來,遞給我。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到處都是警衛,一色青灰制服,但行頭簡單,只是徒手,每座小館至少派定一位。當你拐進暗幽幽的中世紀告解室、古印度廟廊偏房或埃及經卷館,正好沒有觀眾時,必定先瞧見一位警衛呆在那里。

文藝復興館、印象派館,設在頂層的蘇州亭院,男女警衛可就多了,聊天,使眼色,來回閑步。在千萬件珍藏瑰寶中,他們是僅有的活人,會打哈欠,只因身穿制服,相貌不易辨識。人總有片刻的同情心吧(也許是好奇心),當我瞥見哪位百無聊賴的警衛仰面端詳名畫,就會閃過一念:三百六十五天,您還沒看夠么?

警衛長不穿制服,西裝筆挺,巡逡各館,手里永遠提著步話機——閉館了。忽然,青灰色的警衛們不知何時已在各館出口排列成陣,緩緩移動,就像街戰時警民對峙那樣,將觀眾一步步逼出展廳。這時,將要下班的警衛個個容光煥發。

只有那位肥胖的老警衛每次都留住我,偏頭審視摹本:“哈!艾爾·格列柯,不可思議。你保管發財——等一等,這絕對就是那張原作,你可騙不了我!”
老頭子名叫喬萬尼,意大利移民。如果不當值,這位來自文藝復興國的老警衛可以教我全本歐洲美術史呢。

1982年元月,我踏雪造訪大都會美術館,平生第一次在看也看不過來的原作之間夢游似的亂走,直走得腰腿滯重、口干舌燥。我哪里曉得逛美術館這等辛苦,又不肯停下歇息。眼睛只是睜著,也不知看在眼里沒有。腦子呢,似乎全是想法,其實一片空白。
撐到閉館出門,在一處可以坐下的地方坐下,我立即睡著,還清清楚楚地做夢。
但隨即醒來,餓醒的。

記得獲準留學,行前被江豐老師叫去。“不要怕吃苦,”老先生說,“到了美術館,就吃點面包、香腸,這樣子,我們中國的油畫就上去了么!”

后來呢,后來發現美術館闊人區的香腸面包并不便宜,而且美術館內不準吃東西:其實是自己窮。美術館餐廳一份三明治,七八美元,加上地鐵來回票,對當年如我似的中國留學生來說,能省則省。館外小攤有便宜“熱狗”,既難吃,也不果腹。怎么辦呢,于是自備一份干糧,坐在館外慢慢地咽。
幾年后我進館臨畫,索性煮好茶葉蛋之類中國飯菜隨身帶著,僅為在餐廳落座而叫杯咖啡,頗以為得計。有一回剝著茶葉蛋,鄰座來了一家四口工人模樣的日本游客,叫滿一桌,光是每人飯后那份水果,單價就在三明治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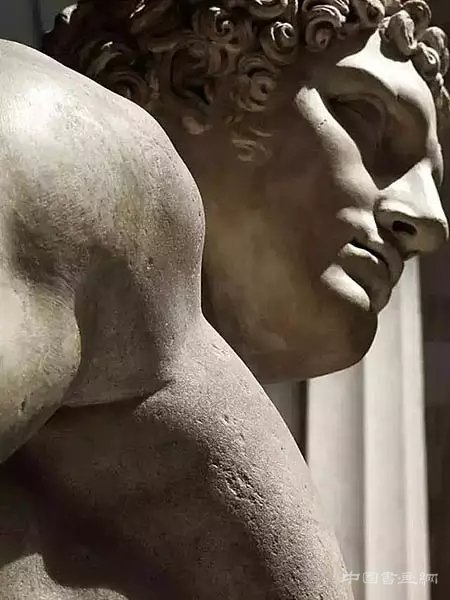
據吳爾芙夫人的說法,若缺了高濃度營養,寫作時腦后那根“火苗”就是躥不上來(難怪“困難時期”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得賞較多的是糧票和油票)。我既非作家,更不是“高知”,乍來美國,腸胃史的內容不過是美院食堂那份菜單:熬白菜、饅頭、白開水。以這點蛋白質、卡路里加脂肪,哪里扛得住逛美術館這類高度體力兼腦力支出的風雅情事。好在美院伙食總算長進了:那年歸國探訪,只見面色活潤的年輕人圍在桌邊,爆腰花、醋熘魚片、番茄炒雞蛋,還叫白酒。
祝福年輕人!如今真喜歡看見青年,常常發現自己在那兒傻看。
